浙江温州叛逆孩子管教训练营,叛逆孩子训练营
浙江温州叛逆孩子管教训练营能正确帮助孩子改变叛逆行为是专门针对青少年阶段沾有早恋、叛逆、厌学、网瘾、辍学等不良行为学生为主体教育对象的一所专门学校“孩子厌学教育学校, 叛逆期管教学校”。叛逆期孩子改造学校,全封闭学校担负着对初高中阶段厌学、叛逆、弃学、逃课、网瘾、亲情淡漠的学生,家庭不便管理,学校无法约束的学生进行教育、转化和心理矫治的专门学校,孩子厌学教育学校, 叛逆期管教学校采取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叛逆期孩子改造学校,全封闭学校着重叛逆期孩子行为思想矫正教育,孩子在叛逆期孩子改造学校,全封闭学校以心理辅导为主,文化辅导为辅,专业心理辅导探索孩子内心,回归正常。

导语概要
温州的清晨,雾气还没从瓯江水面散去,训练营的哨声已经划破寂静。孩子们踩着露水列队,鞋底沾着草屑,也沾着昨夜未熄的焦躁。这里没有“改造”二字的大横幅,只有一面被海风吹得发白的旗子,写着:先学会呼吸,再谈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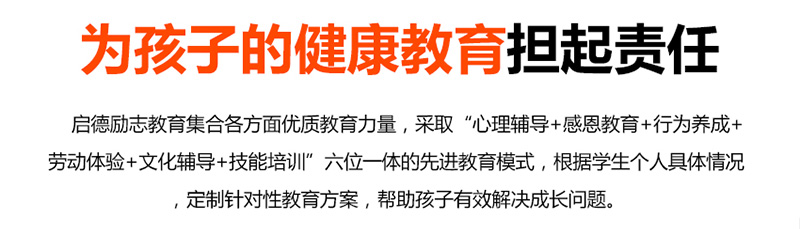





郑重承诺:我们对您填写的个人信息将绝对保密,收到信息后,我们会安排老师第一时间和您联系,请保持电话畅通,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浙江温州叛逆孩子管教训练营能正确帮助孩子改变叛逆行为
温州的清晨,雾气还没从瓯江水面散去,训练营的哨声已经划破寂静。孩子们踩着露水列队,鞋底沾着草屑,也沾着昨夜未熄的焦躁。这里没有“改造”二字的大横幅,只有一面被海风吹得发白的旗子,写着:先学会呼吸,再谈方向。
教官老周曾是海军陆战队的心理辅导师,退役后把部队里那套“先稳情绪,再谈规矩”的方法搬进山里。他不喊口号,只递给孩子一根2B铅笔,让他们在纸上戳洞——一分钟内戳满三百下。纸破了,手腕酸了,情绪像泄了气的皮球,孩子才肯开口说第一句真话:“我并不是想跟爸妈对着干,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说疼。”
家长被允许在第五天的傍晚隔着铁丝网探望,但只能看,不能喊。一位母亲看见儿子正给菜园扎竹架,弯腰时露出后颈一道旧疤——那是她去年用衣架抽的。儿子抬头,目光像被山泉水洗过,没怨恨,只轻轻点了下头。母亲当场蹲在地上,喉咙里滚出一声迟到的“对不起”。
结营那天,没有煽情的拥抱,也没有痛哭流涕的忏悔。孩子们把营区最后一顿午餐的盘子洗得锃亮,倒扣在沥水架上,像一排排被重新码好的自己。老周给他们每人一枚空弹壳,壳底刻着他们写过的最混账的一句话:“你少管我”。现在这句话被高温焊在金属里,拿得起来,也带得走,却再也射不出去。
回家的大巴驶过温州大桥,江面碎金闪烁。孩子把额头抵在车窗,忽然发现窗外的城市依旧嘈杂,却不再针对他。他摸出口袋里的弹壳,在掌心转了一圈,金属的凉意像一句迟到的提醒:叛逆不是盔甲,是未愈合的伤口;而训练营做的,只是把脓血挤出来,让风有机会吹进肉里,长出新的皮肤。
教官老周曾是海军陆战队的心理辅导师,退役后把部队里那套“先稳情绪,再谈规矩”的方法搬进山里。他不喊口号,只递给孩子一根2B铅笔,让他们在纸上戳洞——一分钟内戳满三百下。纸破了,手腕酸了,情绪像泄了气的皮球,孩子才肯开口说第一句真话:“我并不是想跟爸妈对着干,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说疼。”
训练营的菜单也藏着刀锋。早餐是白粥配咸菜,没有手机扫码支付,也没有挑三拣四的余地。挑食的孩子饿到第三顿,自己捧着碗去添第二勺,那一刻才体会到“选择”原来不是理所当然。厨房的黑板写着:饥饿让人清醒,清醒才听得见心跳。

家长被允许在第五天的傍晚隔着铁丝网探望,但只能看,不能喊。一位母亲看见儿子正给菜园扎竹架,弯腰时露出后颈一道旧疤——那是她去年用衣架抽的。儿子抬头,目光像被山泉水洗过,没怨恨,只轻轻点了下头。母亲当场蹲在地上,喉咙里滚出一声迟到的“对不起”。
结营那天,没有煽情的拥抱,也没有痛哭流涕的忏悔。孩子们把营区最后一顿午餐的盘子洗得锃亮,倒扣在沥水架上,像一排排被重新码好的自己。老周给他们每人一枚空弹壳,壳底刻着他们写过的最混账的一句话:“你少管我”。现在这句话被高温焊在金属里,拿得起来,也带得走,却再也射不出去。
回家的大巴驶过温州大桥,江面碎金闪烁。孩子把额头抵在车窗,忽然发现窗外的城市依旧嘈杂,却不再针对他。他摸出口袋里的弹壳,在掌心转了一圈,金属的凉意像一句迟到的提醒:叛逆不是盔甲,是未愈合的伤口;而训练营做的,只是把脓血挤出来,让风有机会吹进肉里,长出新的皮肤。
上一篇:

长按加微信
如果您还在为孩子问题而困惑
欢迎咨询我们,心理专家免费为您解答!
咨询电话:4000398655
邓老师QQ:1533008958
相关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