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百色全封闭叛逆少年矫正学校,叛逆孩子戒网瘾学校
“广西百色全封闭叛逆少年矫正学校觉得和孩子相处陪伴很重要”专门管教叛逆孩子学校,叛逆孩子教育学校 ,叛逆少年学校面向全国招收12-18周岁存在不良行为习惯青少年,“叛逆期管教学校 ,叛逆孩子改变学校”拥有专业拓展训练场地、心理咨询室、沙盘室、篮球场、体能设备、团体辅导室,叛逆期管教学校 ,叛逆孩子改变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同时和多家心理咨询中心和专业教育机构达成了技术支持与战略目标,共同帮扶偏差少年,叛逆孩子教育学校 ,叛逆少年学校正苗启德,12年专注青少年成长教育。

导语概要
百色山里的夜来得陡,像有人把灯绳一拽,整座山谷就黑了。可那所藏在芒果林深处的“全封闭”学校,偏偏在黑暗里亮着一排不灭的窗。窗外是铁丝网,窗里是十二三岁的男孩,正把脸贴在玻璃上,学月亮的圆缺。值班教官不催他睡,只把外套搭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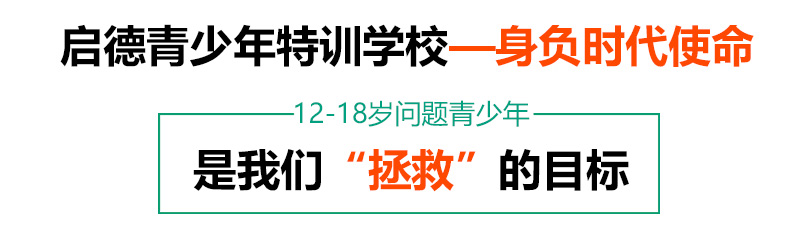



郑重承诺:我们对您填写的个人信息将绝对保密,收到信息后,我们会安排老师第一时间和您联系,请保持电话畅通,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广西百色全封闭叛逆少年矫正学校觉得和孩子相处陪伴很重要
百色山里的夜来得陡,像有人把灯绳一拽,整座山谷就黑了。可那所藏在芒果林深处的“全封闭”学校,偏偏在黑暗里亮着一排不灭的窗。窗外是铁丝网,窗里是十二三岁的男孩,正把脸贴在玻璃上,学月亮的圆缺。值班教官不催他睡,只把外套搭过去,两个人影子叠成一片,像一对被拉长的父子。
这里的人不再提“矫正”两个字,他们说“陪跑”。孩子跑一圈,老师就跟一圈;孩子摔了,老师先不扶,让他躺三秒,再递过去一瓶拧开盖的冰水。那三秒是尊严,拧瓶盖的动作是立场——我在,但我不替你活。
最叛逆的那个孩子,把食堂的饭倒进垃圾桶,转身却看见厨师长在角落啃冷馒头。第二天他最早到饭堂,给每人盛汤,勺子沉下去又提起来,先撇走上面的油,再舀最热的底。没人表扬他,只在黑板报上画了一棵没有名字的树,树干上多了一道小疤,像被勺子磕过。
春天来时,学校把围墙刷成天空的渐变色,从芒果青到晚霞紫。孩子站在梯子上学调色,一笔下去,发现围墙外面还是山,山外面还是云,可云底下多了一个牵绳的人。绳这头系在手腕,那头系在操场,中间留出二十米,刚好够跌倒再爬起。
这里的人不再提“矫正”两个字,他们说“陪跑”。孩子跑一圈,老师就跟一圈;孩子摔了,老师先不扶,让他躺三秒,再递过去一瓶拧开盖的冰水。那三秒是尊严,拧瓶盖的动作是立场——我在,但我不替你活。
有个叫阿立的少年,入校时把头发剃得能看见疤,像一道裂开的地图。心理老师每天陪他画一张新地图:今天用绿色涂希望,明天用红色写愤怒,后天把纸揉烂,再教他展开压平。第七十天,阿立把那张皱巴巴的纸贴在胸口,去操场跑了两千米,没停。晚上他把纸撕成碎片,泡进矿泉水瓶,晃成一杯浑浊的“酒”,敬给老师,说“干杯,我把自己喝下去了”。老师真喝了一口,苦得咧嘴,却记住味道——原来孩子的苦带一点青芒果的涩。

最叛逆的那个孩子,把食堂的饭倒进垃圾桶,转身却看见厨师长在角落啃冷馒头。第二天他最早到饭堂,给每人盛汤,勺子沉下去又提起来,先撇走上面的油,再舀最热的底。没人表扬他,只在黑板报上画了一棵没有名字的树,树干上多了一道小疤,像被勺子磕过。
春天来时,学校把围墙刷成天空的渐变色,从芒果青到晚霞紫。孩子站在梯子上学调色,一笔下去,发现围墙外面还是山,山外面还是云,可云底下多了一个牵绳的人。绳这头系在手腕,那头系在操场,中间留出二十米,刚好够跌倒再爬起。
上一篇:

长按加微信
如果您还在为孩子问题而困惑
欢迎咨询我们,心理专家免费为您解答!
咨询电话:4000398655
邓老师QQ:1533008958
相关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