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泰州叛逆少年改变训练营,封闭式叛逆孩子的学校
“江苏泰州叛逆少年改变训练营觉得和孩子相处陪伴很重要”,正苗启德青少年特训学校采取全封闭式、准军事化的管理,叛逆孩子改变学校 ,不良少年管教学校针对青少年成长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军事拓展、心理辅导、感恩教育、励志教育、传统文化、行为习惯养成训练、法制教育、青春期教育等多元化课程,孩子厌学教育学校, 叛逆期管教学校帮助孩子走出困境,让他们拥有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卓越的品质,在“孩子厌学教育学校, 叛逆期管教学校”成长教育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培养孩子坚强,自信,乐观,感恩,有担当,敬父母,尊师长,爱自己,有责任感的少年榜样!

导语概要
泰州的晨雾还未散尽,训练营的木栈道上已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十六岁的林枫攥着被露水打湿的栏杆,忽然发现砖缝里钻出一簇鹅黄的蒲公英——这个曾在家里砸碎三个手机的少年,此刻正小心翼翼地用指尖碰触颤巍巍的花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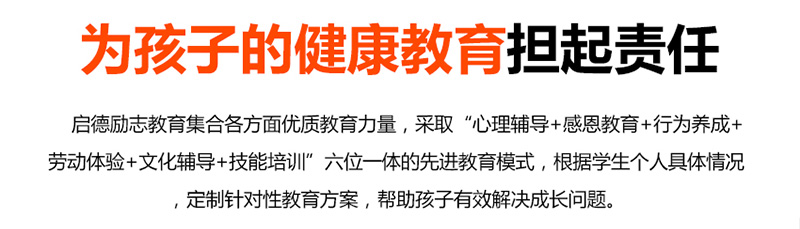






郑重承诺:我们对您填写的个人信息将绝对保密,收到信息后,我们会安排老师第一时间和您联系,请保持电话畅通,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江苏泰州叛逆少年改变训练营觉得和孩子相处陪伴很重要
泰州的晨雾还未散尽,训练营的木栈道上已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十六岁的林枫攥着被露水打湿的栏杆,忽然发现砖缝里钻出一簇鹅黄的蒲公英——这个曾在家里砸碎三个手机的少年,此刻正小心翼翼地用指尖碰触颤巍巍的花瓣。
“我们不做驯兽师。"训练营创始人李骏在茶室煮着陈皮老白茶,紫砂壶嘴吐出的白雾模糊了他眼角的皱纹。窗外是学员们和当地老人一起糊的荷花灯,半成品歪歪扭扭地堆在案几上,"去年有个孩子把灯架全拆了,后来我们发现他是在研究榫卯结构。”
结营那天恰逢梅雨季的放晴。家长们望着晒得黝黑的孩子们展示自制的溱潼会船模型,有个父亲突然蹲下来系鞋带——他的儿子下意识伸手扶住了他摇晃的肩膀。李骏悄悄按掉计时器,原本设计好的"亲子沟通环节"根本不需要了。
在这个没有铁丝网和体罚的训练营里,改变发生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可能是老巷口共享的一碗鱼汤面,可能是修好木船时彼此击掌的脆响,更可能是某个深夜,值班老师默默陪坐在操场秋千上,听着身旁少年断断续续说起被忽略的五年时光。
泰州的月色漫过训练营的黛瓦时,总有些种子在悄悄发芽。
“我们不做驯兽师。"训练营创始人李骏在茶室煮着陈皮老白茶,紫砂壶嘴吐出的白雾模糊了他眼角的皱纹。窗外是学员们和当地老人一起糊的荷花灯,半成品歪歪扭扭地堆在案几上,"去年有个孩子把灯架全拆了,后来我们发现他是在研究榫卯结构。”
水乡的黄昏来得黏稠。染坊里,总爱和父亲顶嘴的小雨正把蓝印花布晾上竹竿,布匹扑簌簌地抖开时,她突然想起母亲梳妆台上的真丝围巾。不远处几个男孩在帮船娘修补渔网,尼龙线在他们指间穿梭如飞——三个月前这些手指只会疯狂敲击游戏键盘。

结营那天恰逢梅雨季的放晴。家长们望着晒得黝黑的孩子们展示自制的溱潼会船模型,有个父亲突然蹲下来系鞋带——他的儿子下意识伸手扶住了他摇晃的肩膀。李骏悄悄按掉计时器,原本设计好的"亲子沟通环节"根本不需要了。
在这个没有铁丝网和体罚的训练营里,改变发生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可能是老巷口共享的一碗鱼汤面,可能是修好木船时彼此击掌的脆响,更可能是某个深夜,值班老师默默陪坐在操场秋千上,听着身旁少年断断续续说起被忽略的五年时光。
泰州的月色漫过训练营的黛瓦时,总有些种子在悄悄发芽。
上一篇:

长按加微信
如果您还在为孩子问题而困惑
欢迎咨询我们,心理专家免费为您解答!
咨询电话:4000398655
邓老师QQ:1533008958
相关资讯